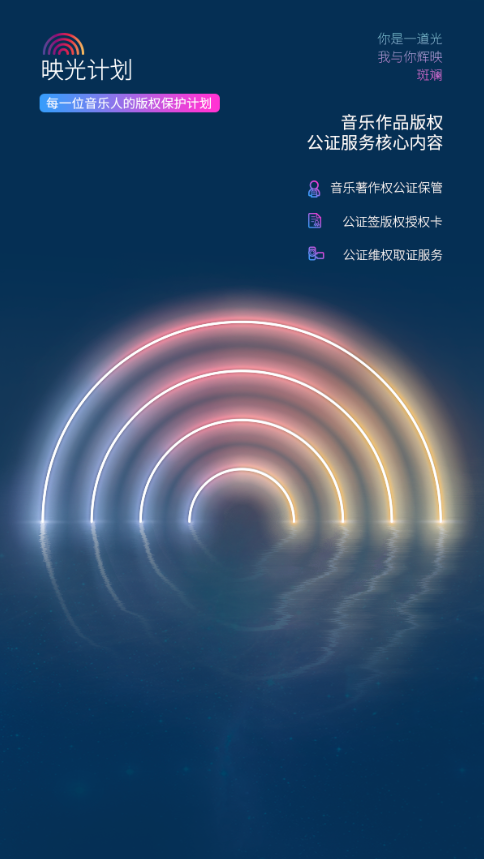曾咏泉专访:音乐人的好时代,伴着映光而来
大晴:
特别专场,中国编曲人茶话会-大晴专访与映光计划联名活动期刊。大言不惭地说,本篇读完可以帮到部分做创作的朋友两个忙,一个是多赚钱,一个是少生气。
大晴:泉哥,讲一讲你作为音乐人的经历。
曾咏泉:家里是我们当地小县城的文化户,爷爷是写粤剧的,带了很多徒弟,算是传统的音乐世家。那时经常去看爷爷指挥粤剧团排练,自认为受到的音乐熏陶还是比较足。但是我小时候没怎么学过乐器,虽然爸爸教拉二胡,可是因为我比较贪玩、静不下心来学。
直到初中,我看到别人弹吉他唱beyond的歌曲,开始对吉他感兴趣,姐姐就送了我一把民谣吉他,结果我因为喜欢吉他,学习耽误了不少。后来经过一番努力,去了南宁市师范学校就读音乐教育专业,到了南宁,我才真正开始正规的音乐学习。
我大致把我的音乐成长之路分为三个里程。
第一个里程,就是进入音乐师范学习的2001年,从这一年起开始学习钢琴,可能和小时候的音乐氛围有关,感觉学起来掌握得比身边的同学快,听到能弹、想到能弹,流行歌什么的一下子就扒出来了,经常给声乐的同学伴奏等等,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后来我也学了小提琴,但不是兴趣使然,坚持不下来,但对后来编曲很有用,因为在学习过程中对弦乐技法有了更深的了解。在这段期间也遇到了很多对我有启发的老师,有曾小珊、陈中、满韵瑶和蓝壮青老师等,借此机会在这里感谢他们。
我们学校那个时候没有作曲课,只能自己买书看和研究,写出一些拙劣的作品出来后,找老师来斧正,慢慢的进步。但是后来我发现,作曲不是一个终极目标,因为作曲之后还要变成声音,要录出来,或者用MIDI做出来。之后,我就钻研到了音乐制作这个版块里。家里也比较支持我,在试探性的询问下,就给钱我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让我做音乐,我猜“估计是玩音乐总好过玩游戏吧”,而且这个过程很正式,让我感动到了。毕竟是2002年,学校里为数不多的人有笔记本电脑,就我专门拿来倒腾音乐软件,大家都不知道我在干嘛,以前接触这些东西的人比较少,现在想起来感觉我算比较幸运。
更幸运的是,蓝壮青老师当时帮我介绍了南宁一个比较有名的录音棚,叫新东西。我在这个录音棚里认识了我的老师,“老猪”朱雪锋,也就是我第一个学习录音的师傅。我开始跟着他学习录音。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录音和音乐制作又是两回事,我还得继续深入学习编曲,录音混音知识对编曲有很好的反哺作用。
2001年-2005年期间,我经常泡在各大音乐论坛,记得当年MIDIFAN论坛还有一些侃大山的板块。我在里面很积极的互动交流,聊一些软件相关的问题,怎么使用,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经常自己钻研后帮别人解答问题,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喜欢,把它当成一个玩的状态,而且又特别有成就感。
到了2007年,为提高自己的专业或者说补学历上的不足吧,我去考了星海音乐学院,在去星海之前,已经在接一些小业务做了。当时一首歌简单编曲大概收个两三百块钱,后来多了需求复杂了也就八百一千的收。在那个阶段我很满足,因为我当时在广州一个月的生活费就六百,一个月偶尔有一些业务来补充,还是很OK的。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我一直在做音乐制作这一块。
大晴:一直是以独立音乐人的身份在做商业音乐吗?
曾咏泉:差不多吧,刚毕业的两年做了一些电视台的项目,参加了一些原创比赛,拿了不少奖。但2009年,对我来说是人生的第二个里程碑。那就是成立了广州数字音乐俱乐部,因为当时感觉数字音乐发展的速度特别快,有很多想进入这个领域的爱好者和学生找到我,他们很难获取这方面的知识,所以我就跟几个朋友专门做了一些免费的音乐沙龙,以科普电脑音乐制作为主,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交更多的音乐朋友。后来从沙龙活动中逐渐发展成了广州数字音乐俱乐部。2010年,我进了一家公司-香港OK STUDIO(广州分部),这个公司在香港八九十年代还算很出名,到了2000年之后唱片不太好做了,这个公司在香港的两家录音棚其中一间搬到了广州,做了分部。我就到里面任音乐总监,遇到了梁炳星老师,深度学习了各种模拟设备的实操知识,开始从事商业音乐制作的领域,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一边在做俱乐部的活动,当时还很担心专业知识的不足,我还专门去北京跟王逸驰老师学习了一段时间,直到现在很多理论基础都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点化。
刚开始工作那几年,在音乐沙龙上分享工作经验和技术,在星海学生会的邀请下,每学期回星海开一些经验分享的讲座,主要是分享各种软件的使用经验。后来发现,这个讲座最重要的环节,是最后的互动过程。很多同学听完课程分享就会来问,现在录音棚好不好做?以后做编曲好不好?赚不赚钱?有点像一个就业指导大会。
与此同时也和几个朋友玩着一支自己的乐队,叫ME-GA乐队,乐队在2012年拿了YAMAHA ASIANBEAT亚洲节拍中国赛区总冠军,当时是在上海的MAO LIVEHOUSE进行的,以为拿了冠军会有机会火起来,但并非如我所愿,可能是没赶上现在乐队的好时代。其实我们乐队每个人都很优秀,现在活跃在圈内的劳国贤老师是当年我们乐队的吉他手,也和我一起到星海做数字音乐科普的讲座;这几年,我看到他有出任薛之谦巡回演唱会的吉他手和周深演唱会的音乐总监,真的很棒,他是15、16年一个人去了北京,才慢慢脱离了乐队的工作,我们在停滞了一段时间后才换人重组,但是激情少了很多,但也还在努力着出作品,现在回想起来,多少有点唏嘘。
就这样,这些科普工作我一直做了到了2015年。现在在线学习很方便,我们已经把很多音乐人转化到微信社群里,广州同城音乐人也越来越多的加入进来,在中国编曲人平台和其他有共识的平台也慢慢建立了全国的新的社群。
我在2015年,还做了自己的音乐文化公司,很多音乐人问过我,做自己不想做的音乐会不会过不了自己那一关。可能很多音乐艺术家们会觉得吧,艺术过度商业化违背了初衷,可能很多音乐人有这种想法,当年我也有过矛盾的心理,后来我觉得我做的就是服务行业,我在满足市场需求、提供服务的同时坚持一定的艺术高度,大概就是谈得妥就做,谈不妥就不做。很简单,不是所有的需求都要被满足,因为甲方在音乐制作领域,可能他的某个需求是很缥缈的,不合常理,我们就帮着理顺、帮着调整、慢慢融入到音乐的业务规范里。说多了哈,你下一个问题是不是要问为什么开始做版权保护?
大晴:不,插播一个问题,录音棚赚钱吗?
曾咏泉:录音棚我做了近十年,换了三次场地,它只是我公司的板块之一,因为觉得有更重要的事要去做,现在托管给了HUGO梁华刚和张俊老师;我觉得录音棚它不是一个能赚钱的业务,艺术家们会说你不要老提钱钱钱的,可实际上真正要经营一个棚,确实要考虑营收的问题;如果服务做好的话,还是能达到一个收支平衡。
但是你知道一个人如果一直在录音,可能工作的前几年还好,时间太久会有一些音乐人容易患职业病,比如抑郁和焦虑。我们俱乐部里的一些音乐人就有这些问题,因为他会发现,录音养活自己是可以,但是赚不了大钱,要在广州这个城市生存、买房、要解决各种各样更高物质需求的时候,是满足不了的。当然你像国内顶尖的录音棚很有名的一些老师,他们的收益应该会好很多,但像行业内中小型的棚和工作室很多,很多都是处在我刚才说的这个状态里。
所以我们录音棚的存在其实是内容工厂的一环,服务他人的同时也服务自己。这个工厂里,不管是音乐制作也好、投售歌曲也好,内容自己运营也好,就是为了把内容建立成一个将来有可能变现的点,就是知产变现。大家也应该看得到,有很多录音棚或者机构都在往这个方向走,大家捎带手的可能连网红直播也在做。
大晴:做版权保护的契机是什么呢?
曾咏泉:我从16年开始做音乐内容的管理,当时有看到未来版权保护这块在大方向上是有前景的,但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做才能做好,直到映光计划的出现。
最重要的契机是有一件事影响了我。2017年有个朋友找到我,给我介绍了一个非常知名,垄断型的大公司的项目(这里就不直说了),给他们做一首歌的编曲,没什么钱,但是内容我很喜欢,是描写春运各职业场景回家或不能回家的温暖画面。因为那是大公司的项目,主题又是写的春运,很快就上了榜,我有要求编曲也署名上名字的时候,说已经上传了改不了,遭到了拒绝。这首作品现在依然还很有生命力,一到过年就很多转发。我当时感觉,大部分音乐人是在行业的底层很弱势,所以在2017年底我决定有机会一定要跨入音乐版权保护领域,为音乐人发声。
你现在看综艺,词曲之后是有编曲人名字,乐手是谁也会标注,现在已经在往这个方向靠了,起码的尊重大家慢慢有了共识。在一个音乐制作团队里面,相比较来说,做编曲的人是最辛苦的。而对于一首歌来说,我觉得编曲才是赋予歌曲生命力贡献的最大存在,因为你要反映什么心情,要靠编曲的风格决定,编曲可以渲染画面感。包括我这边业务现在合作作品版权拆分的比例上来看,词、曲一般是10到15的比例,编曲占到30到40,从这个上面也能看出来,编曲是多么重要的一环。
大晴:编曲的版权比例一般是多少到多少?
曾咏泉:我们在梳理一些音乐人的版权合同数据中,合作作品编曲的拆分比例基本上占30-40左右居多,词曲一共30以内,剩下的就是运营所占的比例。这个比例是根据时间投入、技术成本等等综合评估下的合理分配;当然,这个是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协商的,有些运营MCN直接买断,价格都可以自己谈好。
前几年,版权方面有大鱼吃小鱼,小鱼连虾米也吃不到的各种情况;几次版权大战之后,现在的生态相对来说要比以前好很多。
大晴:映光计划究竟是怎么保护音乐作品的?
曾咏泉:我是18年进入映光计划项目,是我的第三个里程碑,跨界音乐人就是这么来的,哈哈。18年2月份,全国两会上提出要把知产保护提高到一个新高度。恰好身边有在做司法介入知识产权保护试点的朋友,大家都叫他瓜哥,他从省司法厅出来后专门服务公证信息化,延伸出司法公证介入知识产权保护的领域,也符合国家创新政策,当时我就想,司法层面怎么才能更深入音乐行业,所以我参与了这个计划,一起研究一起写方案,过程中不断学习法律知识,让一些新政策新试点方案能服务音乐行业,现在看起来也正在往成功的道路前进。在今年2021年1月1日,映光计划已经接入中国知识产权公证服务平台,版权公证登记已经面向全国免费,而我一直在努力在把这个信息触达给更多的音乐人。
但说到映光计划怎么保护音乐作品的,简单的说就是从源头上。
我们先来倒推一下,音乐人被侵权后会怎么处理?
告侵权方,怎么告?要请律师对不对?这个时候律师就会告诉你,要把证据收集好列出来。你要取证,你就会发现音乐人取证有多困难,你电脑里面还保留着那些创作过程的东西,是OK的,但要请公证员来取证,大概800块钱一个小时(现在的基础费用,每个地方不太一样,有可能更高)。有些已经登记过版权的,你要拿证书出来,拿出来对方可能提出质疑,对方不质疑还好说,一旦提出质疑,你还有很长的流程要走。并且,公证处大家可能不太了解,被质疑的版权证书要做公证书要1500起(量不同价格不同),然后你还要付律师费。总之,流程复杂不说,一般来说,没有个2万块打底维权一定是非常困难的。这就导致很多音乐人压根不敢维权,因为赔的可能都没有花出去的多,除非真的是为了争一口气。
映光计划项目就是抓住了音乐版权纠纷这个取证难、维权贵的痛点,比如以前你可能创作完成一首歌之后再去做一个版权登记对不对。但是映光计划不同点在于可以阶段性保护音乐创作素材,形成创作过程的证据链。你在素材创作的过程当中就可以登记,做一个前置保护,我给音乐人灌输和科普的就是要有前置保护的概念,可以想象成理财、保险什么的都可以。
现在互联网很发达,内容创作过程中未完成的素材流转量非常高,你可能写了一个好词,发给作曲人,但恰巧他没有道德,改了几句就成他自己的词曲作品了,这种情况你怎么办呢?你肯定举证难,花费大。如果通过映光计划,在创作过程里做了阶段性素材登记,再发给别人,如果这种情况下再被侵权,你手上有完整的证据链,你在选择律师的时候手上就有牌了,你找个实习律师赢面都很大,就不会出现取证难、维权贵的情况了。
大晴:泉哥,你刚才说版权登记免费?
曾咏泉:对。今年1月1日映光计划已经面向全国免费了。我们希望通过与中国编曲人大赛合办的音乐版权公开课中再次深入音乐圈,也希望大晴帮我们告诉还在做音乐的朋友们。
今年爆发疫情后一路走来确实不易,借此机会也感谢一些让映光计划快速推进的老师和平台,首先是中国编曲人大赛,两年多的陪伴,实属不易,坚持为音乐人发声和服务。还有王磊老师和袁立斌老师,第一次让映光计划参与到北京现代音乐学院的北音云集原创音乐大赛中,还有音乐人网、NEWP小站、吉他社、音乐窝和《中国好声音》等平台,还有已经加入了映光计划社群的音乐朋友们不断的宣传,你们为映光计划音乐版权保护创新服务续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感谢大家,感谢大晴。
文章出处 https://mp.weixin.qq.com/s/CNiESS9d41_O4qmc6vzrQw
转载新闻请注明出自 Midifan.com